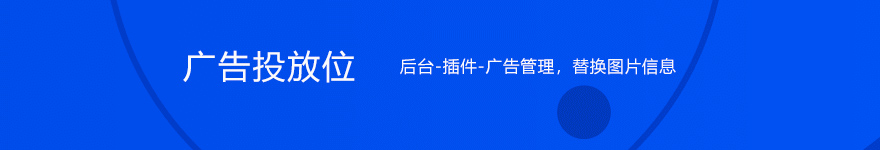在1981年林友仁老師對吳兆基先生的一次采訪錄音中,吳先生說:“古琴雖然是彈撥樂器,但是彈的東西...
在1981年林友仁老師對吳兆基先生的一次采訪錄音中,吳先生說:“古琴雖然是彈撥樂器,但是彈的東西要彈出(弦樂器的)‘拉’的聲音。”
林友仁《平沙落雁》雖然吳先生在講這段話時,目的在于說明右手彈琴出音的音頭不要太重,但是對于左手的滑音來說,這段話也同樣是適合的。兩方面結合起來看,也就是說一首樂曲的音與音之間、句與句之間需要有連綿不斷的感覺,而不能讓人聽起來斷斷續續——在這里我所談論的不是氣息問題,無論怎么彈琴,氣息要求一定是連貫的——我所指的是在聽覺上的直觀感受。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右手方面前文論之已詳,簡單說來,只要是放松之后出來的音,音頭都不會顯得過僵過重;而左手的問題比較復雜,這里或許可以分兩方面來談:之所以容易斷斷續續,第一個原因就是當彈出一個音之后,由于右手不再撥弦,所以在左手滑音的過程中音量其實是在不斷衰減的,這就往往使得下一個音和上一個音在音量上存在一個反差,由此就顯得有些不夠連貫。這一點或許是所有彈撥樂器的共性,但是古琴的特殊之處在于,古琴左手滑音的時間長度往往是超過其他很多彈撥樂器的;因此,如果說其他樂器還能夠借助于右手的快速撥弦而產生一種連貫的感覺的話,古琴似乎就很容易讓人聽起來覺得斷斷續續。
這一問題是否有可能解決?或許關鍵就在于是否能夠意識到左手按弦的虛實:雖然我們經常說“按欲入木”,但是事實上,在走手音的過程中,按弦的力度其實可以是不同的。吳兆基先生在同一次的采訪錄音中說:“滑音在琴背上要走弧線(拋物線)。”這句話似乎很費解,但其實聽吳先生的示范就很清楚:比如說“綽”這個指法,是如飛機降落一般以弧線的方式下落到琴面上取音的,而并不是從一個固定的位置平移到另一個位置。同理,從一個音滑到另一個音時,一開始雖然手指確實是按在琴面上,但是僅僅只是把弦按住而已;而在滑動的過程中,力度也逐漸加強,這就使力度的走向也同樣呈現出類似于弧線的感覺。能夠表現出這樣的虛實,再加上前文所說的走手音加速度的話,那我們就可以發現,在聽覺上走手音在音量上甚至有可能會給人一種漸強的感受。這樣一來,這種音量的漸強感往往就可以和下一個右手彈出的音較為自然地接續在一起,而顯得較為連貫了。
在1981年林友仁老師對吳兆基先生的一次采訪錄音中,吳先生說:“古琴雖然是彈撥樂器,但是彈的東西... 在1981年林友仁老師對吳兆基先生的一次采訪錄音中,吳先生說:“古琴雖然是彈撥樂器,但是彈的東西要彈出(弦樂器的)‘拉’的聲音。” 林友仁《平沙落雁...